(二)80年代后诗人网络诗歌书写的书写策略
面对如此多的问题,我想有必要对80年代后诗人网络诗歌文本的书写策略和生存遭遇等问题展开研究,以便理清思路,找到方向。
在此,先来探讨80年代后诗人网络诗歌书写的主题问题。在阅读了大量的“80后”诗歌文本后,我可以肯定的说,80年代后诗人的网络诗歌书写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有些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就其内容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大主题:情爱、成长、日常和调讽等。这样说是有着根据的,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捏造或自以为是的误判。
就我认为,80年代后诗人最关心的还是情爱主题,这一主题的网络诗歌占据了很大的版面,尤其是大多数新手上路的女诗人几乎脱离不开这个既定的主题。这本是无可厚非的,80后年轻的一代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但还是在传统抒情诗的氛围中继续的延续汉语诗歌应有的脉络。这里面的情可以分为亲情、友情、爱情以及对陌生人的同情等,爱则有着不同的界定,可以是包含深情的情感之爱,也可以是赤裸裸的肉体之爱和充满快感及欲望的狂欢。诗人们为情愁而歌,为乡愁而唱,为性的压抑、苦闷、发泄而歇斯底里的兴奋不已。这些都是情理之中,时代变化了,诗的评价标准也要随之变化,而不能拘束于经典抒情诗的纯洁传统加以排斥。当然,在“情爱”的主题下还掩藏着奢望或可遇而不可求的无奈与踯躅,忧患于黎民之请,沉寂于生命悲欢,这和经典文人的放纵、不羁有着多么的相似,只是改换了场景,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解读秩序。在有意为之或无意透漏中,我们能从80年代后诗人书写“情爱”的诗歌文本中得到生命和人生的颇多感慨,这是幸事,又是诗人和时代无法摆脱的宿命;即使是在高科技统治一切外在现象的网络时代,诗人的内心仍然是隐秘的,有着难以言说却令人感受颇深的灵魂园地。
再说成长主题,这一主题也是80年代后诗人经常书写的主要内容。这与诗人们阅世不深、经历有限是有着很大关系的。传统的成长主题主要是解说为人之一生的苦闷或史诗式的大而无当的宽广的描述;但在众多的网络诗歌文本中,成长有了新的含义,不再是整体的描述或阐释,而成了断裂的艰辛或郁闷的暴发。当然,成长叙事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真实生活的叙述,有梦幻境界的解析,有亦真亦幻的多重置换。但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叙事中,“仙梦”占据了大多数,有关成长的叙述不是理性的分析和刻画,而是多做感性的描绘,借助于神仙法力或精灵古怪去实现自己的想法。这与当今小说新秀们的做法如出一辙,诗人们设置了光怪陆离的场面去战胜自己的苦闷,去获取自己的渴望,在这改头换面的包装下仍然是一颗颗年轻稚嫩的心灵的呼唤和挣扎。这是什么,算是逃避责任或回应现实的极端方式,还是理想和信仰在现实中不可实现时的某种转移的寄托呢。如此种种,幻象成了审美的主要,生活退居后线,当作点缀或学者们研究的铺垫。这是时代的悲哀,还是新文学新诗歌发展的契机呢,不好说,但有一点,当诗普遍的蒙上了梦幻的外衣后,现世的人生渐渐隐退,娱乐和瞬间的享受占据了主流,认识的功用被抹杀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后诗人们在找寻诗歌的生长点时选择了虚幻的梦境,成长变的不那么真诚。这是民族自信心普遍丧失的集中表现,也是可能导致诗歌沦陷的危险因素之一;尽管这可能是未来文学的发展走向,但我们应该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待最新的变化,对于成长主题下场景置换的文本现实不可不防。
至于日常和调讽这两大主题,我想可以从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生活化方面去分析。就前面所说的,80年代后诗人面对的是纷繁芜杂的后工业场面,日常的琐碎是生活的真实,时代文学的主流因素也要求书写现实的实在和可能的实在,何况影视等其他媒体也走向了狂欢化的表面实在,如果再拘束于深刻叙述和深层追求则有悖于时代的发展。因此,很多人选择了日常生活作为抒写的对象,且收效甚好,很多优秀的网络诗歌文本都是在细节的描述和技巧的把握中显示出80年代后诗人超强的实力的。调讽也有着广阔的天地,不平则鸣是我们民族诗歌传统的优良品格,80年代后诗人又是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威猛阶段,“我不狂谁狂”和“人不轻狂枉少年”成了很多人的格言,于是照准现实的腐败和阴暗,集中火力进行深度的打击;但是,诗歌毕竟是诗意的,表述也要在技巧的范围内进行,调侃和讽刺造就了新鲜的诗歌文本,也成就了“垃圾派”等人的创作。这些都是新诗发展的历程,在调讽中展现童年的回忆、抒发未来的情怀、揭露现世的不平是诗歌的题中之意,80年代后诗人学到手了,幸与不幸还在将来。当文学或诗歌真正的实现去意识形态化的时候,调讽主题也许就失去了现实的效力,但作为诗歌技巧还是可以保留的。
以上是分析了80年代后诗人网络写作的四大主题,其中的解读就包含了80年代后诗人的书写策略和生存遭遇问题,我们选择自己熟悉的主题,造就自己时代的主要话语体系,这是时代的必然,也蕴涵着无奈和尴尬的成分。当然因为个人爱好和才力所限,在阐释具体的书写策略和生存遭遇方面必然还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作为整体书写状况和出路的研究还有必要进行下去。
(三)80年代后诗人网络诗歌书写的发展出路
下面谈论80年代后诗人网络书写的出路问题。有一点我们必须相信,只要有鲜明的旗帜,80后群体就可以突出重围,在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和第三条道路占主流的现行诗歌版图上确立自己的地位,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和言说力。诗歌的本性是语言,这毋庸置疑,所谓的诗永远是一段文字,是语言,80后群体的诗也应该是如此。语言是诗歌的原始状态,但不是先验的预设,也不是终极的顶点。以“他们”为代表的民间写作群体曾经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作为自己的旗帜,就我认为这很不合理,这句话犯了形上的错误,将诗和语言给隔离化、主观化、理想化了。当然,这无非是“他们”故弄玄虚的旗帜和口号而已,至于诗的本性是什么,想必大家心知肚明;但是,作为有影响的诗歌群体,这样一个存在明显谬误的观点的提出将会极大的破坏诗的理念,是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在此就不展开说了。再说知识分子写作,这一线的经典作品和大师级人物颇多,几乎占据了学院派的主流,但是有句话不得不说,即“你生活在这个时代,却呼吸着另外的空气”,就诗歌文本而言,某些作品的西化现象实在是太严重了,几乎抹杀了现实日常生活中诗意的存在。至于第三条道路,我认为难成气候,无法和前两种写作相比较,多是些无聊的谩骂和不负责的闲扯,自以为拯救中国诗歌,结果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很难以对网络诗歌的建设做出多少的贡献。
总析之后,我想说的是80年代后诗人要想尽快的发展,必须提出自己的诗歌观点,在和一些潜网多年的80后朋友讨论后,我觉得“诗从语言出发,再回到语言”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也是80年代后诗人可以实践的理念之一。这从语言出发再回到语言是个永不停息的流动的诗歌过程,包括事件、现象、文化、意义、表达机制和显现方式等多方面的重大问题。
上面提到,诗的本性是语言,所谓的诗永远是一段文字,书写在纸制品或电子媒体上的文字。因此,诗必须从语言出发,必须从语言的实在状况出发,借助于语言或文字实现诗的文本性的存在。但是这种出发必须建立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意义趋向上面。诗不但要求书写出来,还要能够以适当的方式解读出来,这种书写和解读是诗的题中之意;否则诗就不能成其为诗。“诗从语言出发,再回到语言”的命题即遵循了这样的理念,普遍顾及了诗的本性问题,适当的解决了诗的书写和解读等一系列的问题,认为诗生活在
书写、传播和解读的流动过程中,而不是凝固在特定的媒介表面做冰冷的他者。
“诗从语言出发,再回到语言”具体的解说如下:“诗从语言出发”,这里面的“出发”是个有所指向的过程,语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多向的置换过程才能够成为诗的语言,才能在大众的视野中“再回到语言”,回到诗的实在状态。在这个流动的过程中,事件以及事件的集合“事件串”是必须经历的第一站。就我认为,诗的书写必须从事件或事件串出发,从活生生的现实状况出发,必须立足在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上,以个体事件的描述或事件串的整体总结为基础从而构造具有现实生命的诗的语言。叙事诗是这样,抒情诗也应该是这样的。这就要求我们的80年代后诗人在网络诗歌书写时必须从细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从生活中的事件或事件串出发,通过诗的不同状态在不同阶段的流动去建设诗之本性的意义;而不是预先的设置诗的意义或主题,或者根本就抛弃日常生活中本来拥有的诗意因素。
诗经过语言、事件或事件串后到达现象,这里的现象是是同一首诗或一系列诗的多重事件的复指,也指一切诗歌文本中相同或类似事件的整合;诗人在书写时不应该拘泥于一角,而应该从整体出发,尽量给自己的诗歌文本找到恰当的定位,使之依存于现象,而不是突兀的在事件的范围内旋转。诗人还必须把诗放在一定的情景中才能把握诗的内蕴,而这种情景是需要诗歌语言去构造的。诗人用语言构造情景,读者也从语言出发寻找情景,诗人和读者在情景中实现碰撞,从而有可能进一步的书写和阅读。而就我认为呢这种情景呢就是此处的现象,这样的情景是深入诗歌书写和阅读的第一次交锋,是诗意追寻和释放的必然,只有作者和读者共同的努力才能够使诗真正的成其为诗。同时要指出的是,这种现象或诗人用语言构造的情景并不同于中国古典文艺学所说的意境或境界,情景只是语言描述的事件或事件串在诗意旅途上的进一步构造,而不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丰富的意义集合体;在此还没有意义可言,只能是诗意的萌芽时期或初步的构造阶段。
现象之后是文化,在此处的文化是现象集合后经过权力删除或挑选后所形成的一定区域或民族的显性的整体生活方式。这种文化必然有其独特性,但也应该消除其附加的神圣性光环。诗人在书写的过程中经历文化,这是每一首诗产生所要求的必然,而且文化作为诗人书写的场地,有着极其重要的限制或保护作用;只有符合特定的整体生活方式或文化的诗才是真正的诗。知识分子写作的某些诗歌因为脱离了现实的生活方式和民族现行的文化,不可能引起太大的效益,也不可能对民族诗歌大发展起到多大补益。认识到这一点,80年代后诗人在网络诗歌书写时必须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进行,而不能过度的超越或无限的推延;这是诗的内在要求,也是诗意存在的必然。因此,80年代后诗人要牢记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不能有所抛弃或做出无畏的逃避。当然,披着汉字外皮的洋诗是不算数的,顶多有着娱乐效用或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
只有在文化范围内书写才可能有意义,在我认为,意义是诗最终的志向,也是诗人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的最后驿站。但诗歌的意义是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在书写和阅读中不经意间的突现,并不是诗人赋予的或读者解释的,同一首诗在不同的时代可能有着不同的意义,这与诗人写作的文化背景有关,更和读者解释所依赖的文化背景有关。意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流和对话,是诗人和读者灵魂沟通后的产物;凝固的媒介状态的诗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对应于80后群体,我们在书写的初始并不要给以诗以意义的预设,等到进入流通领域后,诗的就会有自然而然的意义,这并不是承认与否的问题,事实就是如此,任何人不可以违背。
还有就是意义如何出来的问题,这就需要80年代后诗人在诗歌技巧和技艺方面多下工夫了。诗意并不是随便每一首诗的书写和阅读所能拥有的,只有在那些符合民族语言规范又包含高度技巧和技艺的诗歌文本中才能体会的到。诗歌语言中所蕴涵的诗意要流动出来,必须要有合适的途径,这就涉及表达机制和显现方式问题。表达机制和显现方式是诗从作者到读者的最后一环,也是诗人最后的承担责任的领域。高明的诗人要在技艺技巧方面多努力,否则以前所下的工夫都是徒劳的。现阶段,汉语的表达机制和显现方式还处于转型时期的混乱过程中,要想有所突破,必要的训练是应该的。80年代后诗人也要加强运用诗歌语言的技巧和技艺,只有现行民族语言运用的纯熟了才能够写出可读的耐读的网络诗歌。到此,诗的流程已经回到了语言,我们的旅行也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
以上我谈论了“诗从语言出发,再回到语言”的具体解说,当然,理论的阐述是苦涩的,其中必然有不完善之处,但不是错误或失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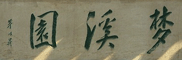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独立宣言版主
独立宣言版主
 Post By:2005/10/26 17:13:4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5/10/26 17:13:42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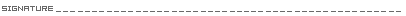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独立宣言版主
独立宣言版主
 Post By:2005/10/26 17:14:11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5/10/26 17:14:11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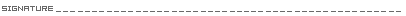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独立宣言版主
独立宣言版主
 Post By:2005/10/26 17:14:28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5/10/26 17:14:28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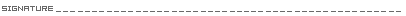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独立宣言版主
独立宣言版主
 Post By:2005/10/26 17:15:1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5/10/26 17:15:16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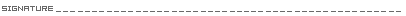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5/10/26 18:12:14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5/10/26 18:12:14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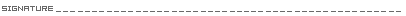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独立宣言版主
独立宣言版主
 Post By:2005/12/3 10:55:1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5/12/3 10:55:16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5/12/18 14:18:19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5/12/18 14:18:19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