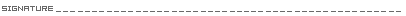鲜血就要诞生
——评水剑狂刀的《石头森林》
现代汉语发展到了我们这个年代,许多的字、词、短语、句子似乎是长了腿,不再按照人们熟悉的既定方式结合,而是忽来忽去、腾挪跳跃,让人无法捉摸。于是乎,写诗难,读诗也难,想要读懂七、八十年代出生的诗人的白话新诗更是难上加难。但是,这并不是说,现在的新诗无法解读,如果选好了角度和切入点还是可以体会到其中的味道的;下面我就尝试从人类学的角度去解读水剑狂刀的这首《石头森林》。
首先来看这个题目,“石头森林”,这样的命名很容易让人想到水泥钢筋铸造的现代城市和极端物质化的现代人类的生活症状。诗人是不是意在如此呢,通读之后便可得知。
“那些星星的尸骸,高举火把”,“星星的尸骸”是什么,和“石头森林”有什么关系,它们为什么要“高举火把”,寓意何在?就我认为,这“星星的尸骸”一方面是自然的状态,星星陨落到地球之后成为陨石,而“石头森林”正是那些石头的构造物,这是水泥钢筋铸造的现代城市;另一方面呢,我们说每一个人都对应着天上的一颗星星,“星星的尸骸”就是活生生的每一个人,他因为罪恶被贬斥来到人间或是因负有伟大使命而降临人间,而这人间就是使人所谓的“石头森林”,这是极端物质化的现代人类的生活症状。因此,诗人用一句“星星的尸骸”从不同的层面寓意了“石头森林”的双重韵味,令人叹止。为什么要“高举火把”呢,这是对于动作的描写还是幻象的渴望呢,都是,在诗人那儿充满激情,饱含温暖,这个处于“石头森林”之中的人类社会或许还有救。
诗人在第一节中给出了“石头森林”的不确定解释,“石头做的村庄//我石头一样的亲人//响水已经喑哑。我的亲人//最高处的石头唱着歌//不是给我们的。”“石头做的村庄”,这是物的客体的方面说“石头森林”,“我石头一样的亲人”,这是从人的主体的方面说“石头森林”,但是,“响水已经暗哑”,整个世界充斥冷漠、疾苦和罪恶,石头是坚硬的,生活的环境是坚硬的,人心也是坚硬的,诗人似乎已经打算放弃追求和希望,因为“响水”也停止了呼唤和涌动。此刻,“我的亲人”处于无奈和痛苦之中,他们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痛苦,这令诗人更是痛心疾首,无可言说。“最高处的石头唱着歌”,这“最高处的石头”,如前所说,是星星,是村庄的高点,也是人类的高层,在此,诗人用充满批判的话语刻画了人与自然的斗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同时,因为这歌唱“不是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显得更加漠视和孤单。“我们”是谁,我和我的亲人,还是星星,还是无意义的实体,无寄托的虚无呢;我们是不配享有歌声,还是根本就无法去享受歌声的魅力呢?诗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诗人的心情是沉重的,但是诗人毕竟看到了希望。或者是石头,或者变成石头,在这散漫的石头森林里还有着歌唱,虽然此时的歌声不是给我们的,但那却 构成了是“我和我的亲人”的终极追求。有追求,有信心,还有新生的可能。
接下来,诗人宣告:“做低头行走的动物,我的亲人//在夏天炎热,在冬天寒冷//春天从不曾长上身体,//我们从不谈论收成”,夏天炎热,冬天寒冷是正常的季节效应,而春天呢,“从不曾长上身体”,秋天呢,“从不谈论收成”。本来是四季分明的时代,却显得那么的严寒酷暑,没有春天的播种和辛劳,没有秋天的收获和喜悦,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似乎这就是“石头森林”的症结所在,人们习惯了冷热,却对于温暖不屑一顾;但是这种“不屑一顾”是人们出自本心的吗?绝对不是,诗人说“做低头行走的动物,我的亲人”,诗人在劝告,或是在描述一种生活的现状;其中这个“做”字用得很有味道,“做”,在新华字典中有七种意思,与这里的诗意相近的有三种,一是“干,进行工作或活动”,一是“当,为”,一是“装,扮”等,在此,我倾向于“装,扮”的意思,因为在诗人认为还是有希望有可能的,而“我的亲人”呢,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生活的困顿和雷同。至于诗中没有出现春、秋的概念,我觉得这是诗人在有意回避生产和劳动等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方式,这是诗人的预谋,因为在“石头森林”里一切都是坚硬的,即使人类活动也是如此,诗人无疑是在做些愤怒但又无可奈何的回避,也算是种叙述的策略吧。
至此,在诗人的叙述中,“石头森林”的艺术形象已经清晰可见,那就是“坚硬、冷漠、困顿”,“石头森林”封闭了“我”和“我的亲人”,“我的亲人”和“我”又是“石头森林”的铸造了者,在这相互关系的坚硬、冷漠和困顿中,人类按照现在的生活和生存方式是无法走出去的,这就是诗人给出的答案;但是诗歌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到此结束,新的问题接踵而至,试问,“我”是否也应该和“我的亲人”一样呢,“我的亲人”又是哪些呢,他们又在忙些什么呢?
要回答这些疑问,还需要回到诗歌本身。诗人在第三节写道“ 我还会高举手臂,象//所有的石头那样呐喊,//我还会做白色的植物,//从不死去//不会醒来”,诗人要“高举手臂”,“呐喊”,“像所有的石头那样呐喊”,原来我的亲人都是些石头,在此,人被物化成了石头,他们还在“呐喊”,不知道这呐喊是徒劳的还是应命的呢,总之是呐喊,有些声音,自己的声音,或者他人的传声筒。“白色的植物”,也就是石头,他们“从不死去,不会醒来”,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生和死是一样的,只是言语符号理解的差异了,症状相同,生活也就是另一种死亡。这么悲哀,对于敏感的诗人,更是难以接受,所以“我”高举手臂呐喊,尽管徒劳,尽管无益,可对于“我”认可“我的亲人”来说,只能如此。在此,“石头森林”是没有生命意识的,这一节的描述也似乎和“石头森林”无关,但是,原来的人群在沉睡,在沉睡中无声无息的消失;只有灭亡才能取得新生,这是诗人的逻辑所在。
下面这一节诗人感情的自然延伸,诗人在此造就了世界灭亡时的景象,虽然用了相对优美的文字,底色却是幽暗寒冷的。“那些长满石头的黑色树木//正在成群的行走//占领河流山川//占领天空//世界即将成为果园//我们即将丰衣足食”,诗人借助拟人的手法,写了“长满石头的黑色树木”的一系列动作,成群结队的行走、占领河流山川、占领天空,这样的描述不由得使我想起了美国电影《魔戒》中的场面,大批的邪魔妖怪进攻人类是似乎就是这样。诗人是不是受到了《魔戒》的影响呢,我想诗人是看过《魔戒》的。然而,场景如此,诗人的描述却是延伸到了另外的地域:世界即将成为果园,我们即将丰衣足食。悖论,诗人痛心疾首之后,做出诊断:意识消亡,物种灭绝,人化为物。在这一节中,我们注意到,诗人用了一句“长满石头的黑色树木”,黑色对应白色,上一节曾经提到“白色的植物”,这一黑一白恰巧是白天和黑夜在诗歌中的具体的显现,“植物”与“树木”相映,共同钩沉了这不断消失的过程。然而最使诗人恐惧的是世界大同,个性灭亡,正如诗中所写的“世界即将成为果园”,人类重新回到没有智慧和争斗的伊甸园时代,岂不悲哉!在此,参与者和旁观者都是必然的,没有例外,都是心灵和肉体的必然承受。
于是,诗人提出了最后的请求,“ 请允许我死亡,我的石头亲人//请用暗紫色的泥土葬我”,既然死亡是我唯一的选择,如果我的死亡能拯救人类的消亡,那还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呢?诗人决定献身,充当一个救世主的伟大角色。在这一句中,请注意“允许”的用法,尽管诗人意识到了人们(“我的石头亲人”)的冷漠和坚硬,诗人还是做到了作为人类的一员应该做到的礼仪和规范,当然这只能是遐想,是诗人一厢情愿的憧憬;但是,浪漫是诗人的天性,诗人还有自己的想法,“请用暗紫色的泥土葬我”,暗紫色?这是生命的色彩,失去光泽的生命也只能用暗紫色的泥土埋葬,掩盖风流,从头再来。“鲜血就要诞生,//我所有的孩子//都会身披霞光”,诗人是企图用自己的死亡换取人类的重生,如同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诗人要用鲜血浇灌大地,洗刷罪恶和坚硬,唤醒沉睡的美好与和谐,让“我所有的孩子都会身批霞光”,然而这霞光,是朝霞还是晚霞呢,是诗人生命的回光返照,还是在诗人死后,“我的石头亲人”在祭拜“我”时做出的最后的挣扎呢?我认为,诗人在最后的结尾部分处理得不很合适,虽然打开了诗歌理解的界限,但是却使得理解变得模糊,变得不那么明确,让人费解!至于无法阐述的一系列的问题只好留给未知,因为诗人没有表明,我们也不好推论。诗人的想法是美好的,崇高的,甚至是伟大的,但愿有所成就。诗人向往着“石头森林”里的“黑色树木”和“白色植物”都变成“身批霞光”的“我所有的孩子”,显然是对应了“那些星星的尸骸,高举火把”;诗人在诗歌的开始就预测了结尾,却没有完成,似乎有删节。
通读全诗之后,我觉得诗人的思想深度和表达力度是足够的,但是,有些地方略显晦涩让人难以理解,至于“诗无达诂”,只好如此!
附录:石头森林(作者:水剑狂刀)
引子
那些星星的尸骸,高举火把
1
石头做的村庄
我石头一样的亲人
响水已经喑哑。我的亲人
最高处的石头唱着歌
不是给我们的。
2
做低头行走的动物,我的亲人
在夏天炎热,在冬天寒冷
春天从不曾长上身体,
我们从不谈论收成
3
我还会高举手臂,象
所有的石头那样呐喊,
我还会做白色的植物,
从不死去
不会醒来
4
那些长满石头的黑色树木
正成群的行走
占领河流山川
占领天空
世界即将成为果园
我们即将丰衣足食
5
请允许我死亡,我的石头亲人
请用暗紫色的泥土葬我
鲜血就要诞生,
我所有的孩子
都会身披霞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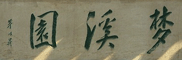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独立宣言版主
独立宣言版主
 Post By:2006/4/10 19:44:3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6/4/10 19:44:30 [只看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