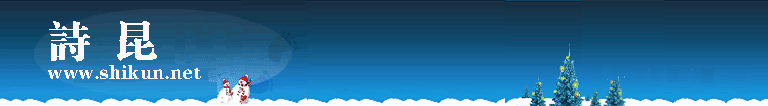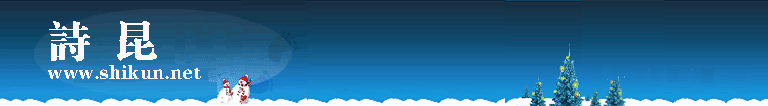| 董国军
诗歌是辉煌灿烂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最耀眼的珍珠,在诗歌发展的长河中,产生了唐诗宋词的高峰,也产生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伟大的诗人词家。新文化运动中,新诗以反传统的姿态横空出世,并成为现代文学中诗歌的代表。一百余年来,传统诗词为进入现代文学主流,一直存在着改革的声音,从“旧瓶新酒”,到中华新韵,再到中华通韵,对诗词的改革似乎都在“改”上,但诗词与大众的距离,始终如盈盈一水间隔望着的“伊人”。反观新诗,虽然热热闹闹,但走到今天,也不免出现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的悲叹。特别是,最近一些所谓的文学大奖,评出的所谓的新诗名家,除了自嗨之外,与芸芸众生间已渐觉形同陌路。现代汉语诗歌的出路在哪里?现代汉语诗歌还能不能承续古典诗词曾经的灿烂辉煌?这是当代诗歌理论研究与创作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古典诗词的传承来说,语言环境变化了,古典诗词必须要变,从诗词曲的产生过程来看,需要诗人们从大众喜闻乐见的俗文化中发现、提炼、产生新的诗体。民国时期,林琴南先生有“新乐府”的探索,后来如启功先生的“韵语”,丁芒先生的“自由曲”等,都是在此一方向下的某种探索实践。从新诗的发展来说,虽然是以反传统出现的,但所谓“逆取顺守”,新诗的发展,需要观照传统,吸收古典诗词中的精髓,提升新诗的艺术性。闻一多先生提出新格律诗,并强调新格律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也是对新诗的一种最原始的探索实践。
应该说,古典诗词与新诗的出路,是相向的,诗词要从传统走向现代,新诗要从现代观照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的交汇点所在,就是现代汉语诗歌追寻的定位点之所在。笔者之一的董国军先生,长期从事诗词创作,在诗词创作实践中逐渐提出了“继承传统,别创新声”的想法,而韩陈其先生作为汉语言学教授,更是提出“在言意象观照中探寻汉语新诗格律”的具体路径,并身体力行,先后出版了《韩诗三百首》《韩陈其诗歌集》两本诗歌集。
笔者认为,诗是由一定节律的“言”、一定情感的“意”、一定范域的“象”构成的“言—意—象”的聚合体。“言”是诗之形。节律作为诗之形的组成之一,不仅包含音节节律,而且还包含所谓音韵节律、语义节律、语法节律。抛弃了“诗之形”的现代新诗,其实质就是一种自我抛弃,因为无以为形的新诗,其本身必然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窘境。“意”是诗之境。诗要表达一定的情意,呈现一定的意趣,创造一定的意境。但要表“意”,离不开“象”,“象”是诗之魂。
象是中国哲学与美学中的重要命题,老子提出“大象无形”,《易经》提出“立象以尽意”,对魏晋美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到唐代,薛璠提出“兴象”,王昌龄、刘禹锡等提出“象外之象”——境。笔者在继承中国优秀诗歌传统,吸收西方诗歌文化基础上,构建了基于“万象”的“三象之说”:自然之象、人工之象、精神之象。而精神之象则有印象、意象、大象之由浅入深的和由有形入无形的认知过程和梯度变化。诗歌创作与释读的过程,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象思惟的思惟过程,即一种依据观象、取象、立象的顺序而渐次展开的思惟过程。因此也可以说,诗歌创作与释读就是一种观“象”思惟,就是一种取“象”思惟,就是一种携“象”而行的立象思惟, “言”“意”一脉,“意”“象”一体,“言”“象”一统,借言释象,以象见意,以意筑象,三象流转,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
汉语诗歌创作,无论古今,其核心都在于想“象”, 对“象”的“想”,就是一个诗歌创作或释读的过程,也就是象思维的观象、取象、立象的过程;就是若干个“言”“意”“象”错综复杂的复合和融合的过程,其成功与否,其实就是取决于 “言”“意”“象”复合和融合的信度、程度、深度、广度、粘度、密度等等。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歌既要言志与永言,就必然离不开“律”。传统诗词于律过于精细,不免让人有束缚之感;而新诗则如脱缰之野马,完全丧失了其作为诗的自我所在。因此,有理由相信,在研究汉字、汉语和古今诗歌的基础上,在言意象的观照中探寻创制汉语新诗格律,诚为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
笔者把“象”作为汉语诗歌灵魂,构建现代汉语诗歌新格律,比较成熟而全面地把握中国现代诗歌的形律、句律、视律、听律、象律,形成了现代汉语诗歌的齐正体、宽骚体、宽韵体、宽对体、宽异体、如如体……并积极从事创作创作。或别创新声,先后创作了近于传统词曲而不再有平仄束缚的《华容道》,接近于新诗而又颇具新格律经营的《静夜思》等新声作品。相对于前人的探索,在继承古典传统的基础上,更具形式的自由性与内涵的开放性,更注重于意象之经营,有意无意间,在传统诗词与新诗之间,构架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当然,这种理论与实践永远在路上。一种文体格律的产生,需要一个时代一批人的努力,需要有伟大的作品为之奠基。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