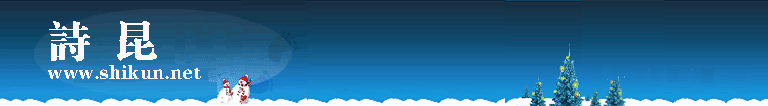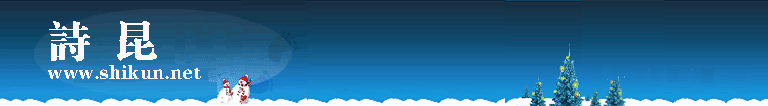| 昆阳子
清平调
其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其二 一枝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其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太白《清平调》三首,创作背景在唐代李濬《松窗杂录》记录甚详细:“开元(当作天宝)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沈香亭前。会花方盛开,上乘月夜诏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笺赋之……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敛绣巾重拜……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
这三首诗是应制之作,也是应急之作。作为应制,要贴合名花、妃子,当然更要能合圣意。说是应急,是玄宗临时起意,游园赏花,而其间不想听旧乐府,要宣李白进《清平调》三章。这边等着用呢。李白虽然宿酲未解,但本来也能“斗酒诗百篇”,又是皇上宣赐,还是很快就创作出来了。就现场效果看,玄宗与太真妃子杨玉环都很满意。因为有这个故事,这首诗历代评之者甚多,有些又不免过于穿凿,而有些更是隔靴搔痒,挠不到痒痒处。 作为联章的三首,首先从整体上看,全诗将牡丹与太真结合起来写,每首又略有侧重。第一首由花容而想到人貌,并用群玉山头、瑶台月下的神仙来作比拟。第二首将花与人合写,以巫山神女、汉宫飞燕之不如来作比较。第三首正写沉香亭畔宴会之乐,实有花不如人之意。有说这组诗暗含讽意,恐不足为据。应制之作,又是急就,应该不会也不敢考虑置入许多隐晦内容。但中间一些比喻,确实容易授人以柄。如李濬《松窗杂录》后面其实还有一段话:“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诗,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斯!’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这其实也是太白写诗经常容易出现的毛病。这个影响仕途还是好的,因为《永王东巡歌》还差点丢了性命。 这里主要是想谈谈第三首如何理解“解释东风无限恨”一句。“解释”是消释的意思,一般的理解,都是把“春风”指代玄宗皇帝。如朱谏《李诗选注》说:“名花国色岂徒自相欢爱自己,吾君亦长爱之。带笑而看之,殊无致也。当此春风之时,解释万机之虑,能使吾君胸次怡然,无有可恨者,其在沈香亭北倚阑干之时乎!对妃子赏名花,相忘于宵旰之外,其乐固无涯矣,又何有于留恨乎!”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卷二十亦言:“本言释天子之愁恨,托以春风,措辞微婉。” 朱谏之解已自带疑问。刘学楷先生在《唐诗选注评鉴》一书中提出了新的解释:“解者因首章次句‘春风拂槛露华浓’中的‘春风’‘露华’有象喻君主恩宠之意,故连类而及,认为‘解释春风无限恨’中的‘春风’即君王的象征,认为此句是说玄宗的无限愁恨均因‘赏名花,对妃子’而消释。这恐怕有些拘执。一则君王的恩宠不等于君王本身,不能以彼例此。二则在‘春风拂槛露华浓’的诗句中,写实与象征是自然融为一体的,读者从浑融的意境中自然可以体味出‘春风’‘露华’的象喻意味;而在‘解释春风无限恨’的诗句中,若以‘春风’为君主的象喻,则显得非常生硬呆滞。且上句既言‘长得君王带笑看’,则君王又有何愁恨之可言,更不用说‘无限恨’了。不但君王无恨,‘春风’亦无恨。实际上三、四两句并非写君王无恨,凭栏赏名花对妃子,而是写春风吹拂下的牡丹含苞怒放,倚栏摇曳飘舞的情景。花含苞未开时固结不解,有似女子之脉脉含愁,故李商隐有‘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之句。所谓‘解释春风无限恨’,即指和煦的春风解开了牡丹无数包含在花苞中的情结,使之朵朵迎风怒放。钱珝《未展芭蕉》有‘一封缄札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拆看’之句,亦可参悟,而‘沈香亭北倚阑干’中的‘阑干’,亦即‘春风拂槛’之‘槛’。而一曰‘倚阑干’,一曰‘拂槛’,所指者均为牡丹花在春风吹拂下摇曳飘舞、倚阑拂槛的情景。而写牡丹之含苞怒放,倚阑拂槛,亦正所以象喻杨妃在玄宗的恩宠下更加光艳照人、婀娜多姿的情状,写花而人即寓其中。由于‘解释无限恨’只是对牡丹含苞怒放的一种象喻,则对‘无限恨’的内涵就不必再去计较追究。否则,无论是说玄宗或杨妃‘无限恨’,都无法讲得通。” 刘学楷先生对“春风君王说”提出了质疑,而提出“牡丹贵妃含愁说”。但无限恨者为何,亦是说不出,道不明。 要正确理解“无限恨”,还是放到三首诗、特别是第三首诗中间去整体上理解把握。前面对三首诗之间的关系,简要作了说明。就第三首,应该是“人胜牡丹”意。第一句“名花倾国两相欢”乃合写名花牡丹与倾国妃子相应生辉,第二句承首句,写君王之畅怀,点出宴乐之核心主体“君王”玄宗。第三句转折,是全诗关键,这里的“春风”其实没那么深奥曲折,就是写“春风”,只是把自然无情之春风,化作有情之春风。“春风无限恨”者为何故?牡丹花开,本在春暮,春之有涯,花之有期,转眼皆为阑珊矣。而能“解释”“春风”之“无限恨”者,原乃太真妃子耳。第四句“沉香亭北倚阑干”用倒叙作结,正面单写太真妃子,既言容比名花牡丹,而又更能青春永驻,日日伴得君王“带笑看”,此本是恭维太真妃子,讨好玄宗皇帝的话罢了。 第一首“春风拂槛露华浓”写太真之得宠的客观背景,第三首“沉香亭北倚阑干”照应“春风”一句,言其胜花,而长得君王带笑看者,则是从诗人或是旁观者角度慕其得宠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