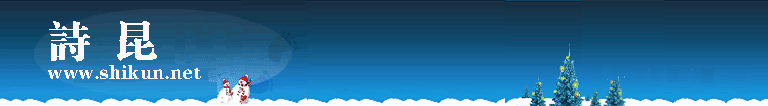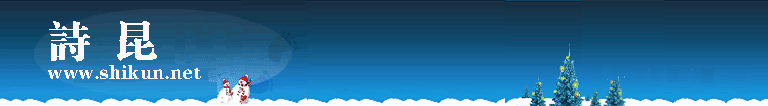杜甫《登高》诗学习札记
昆阳子登高
唐·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老杜《登高》七律,格律严紧,气魄宏大,古来评鉴者最多。评鉴既多,不免有褒之者,亦有贬之者。中间影响最大的当为明胡应麟《诗薮》语:
杜“风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古人,后无来学。微有说者,是杜诗,非唐诗耳。然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律第一也。(元人评此诗云:“一篇之内,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亦有识者)又曰:若“风急天高”,则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而实一意贯串,一气呵成。骤读之,首尾若未尝有对者,胸腹若无意于对者;细绎之,则锱铢钧两,毫发不差,而建瓴走坂之势,如百川东注于尾闾之窟。至四句用字,又皆古今人必不敢道、决不能道者,真旷代之作也。然非初学士所当究心,亦匪浅识者所能共赏。又曰:此篇结句似微弱者,第前六句既极飞扬震动,复作峭快,恐未合张弛之宜,或转入别调,反更为全首之累。只如此软冷收之,而无限悲凉之意,溢于言外,似未为不称也。 言不足者,从内容上,主要说尾联结得有些弱。胡应麟对此也有很好的辩解。虽不能堵后来悠悠之口,但胡评有理论,自当确论。以老杜当时境况,登高寄慨,雄浑苍茫,全出自于胸中抱负所在,但世事如斯,怅怀难释,对之者亦唯酒耳。前之悲壮,结以阑珊语收之,则愈显人生之无奈者。今人一见古人借酒浇愁,或者乐天知命,便言消极,不知人生本有进退、悲喜,本不以之区别诗中高低者也。 清朱瀚《杜诗七言律解意》从章法的角度,对尾联之妙也进行了比较精到得评鉴。朱瀚说:
律贵匀稳,亦须著一、二得力字面,即通体生动,如武帝《秋风词》、荆轲《易水歌》,神采全在“风”字,此作亦尔。起手二字,是其得力处。惟“风急”,故猿啸哀绝,鸟飞却回,落木为之萧萧,长江为之滚滚,此传神法。“艰难”应“作客”,“霜鬓”则又年老,何堪萍转!“潦倒”应“多病”,止酒倍加寂寞,何以消愁!此进步法。胡元瑞(胡应麟)谓结联为软冷,此隔靴之见。 清何焯《义门读书记》所谈也非常有卓见。何焯说:
远客悲秋,又以老病止酒,其无聊可知。千绪万端,无首无尾,使人无处捉摸。此等诗如何可学!“风急天高猿啸哀”,发端已藏“独”字……“潦倒新停浊酒杯”,顶“百年多病”,结凄壮,止益登高之悲,不见九日之乐也,前半先写登高所见。第五插出“万里作客”,呼起“艰难”,然后点出“登台”在第六句中,见排奡纵横。 言不足者,从格律上,主要说通篇对仗,使得通篇板滞,缺少灵动。如清黄生《杜诗说》言:
前景后情,自是杜诗常格。起联转联,并三折句,工整有力。结联宜稍放松,始成调法。今更板对两句,通体为之不灵。《九日》《恨别》《野望》诸诗,并不得登甲集,皆以起结欠灵故也。 此说很有杀伤力,对仗既多整肃,则易少灵动,此为常识。但许印芳《瀛奎律髓汇评》引文所说:“七言律八句皆对,首句乃复用韵,初唐人已创此格,至老杜始为精密耳。老杜诗中集大成者,于格律亦颇细密,不会不知,而用四个对仗者,本欲险中求变求新。至于手段,或如清张谦宜《絸斋诗谈》说:
《登高》通体用紧调,雄健严肃,七律第一格。体紧调最不易学,其声色气象齐到处,正是养得足。 “养得足”,不只笔力,更在心胸。此诗既高屋建瓴,又得元气贯穿,浑莽一气,虽不觉滞碍。但除却这方面,笔者觉得,在对法上,七八句也有独到处,竟然似对非对,不对而又成对。如何说呢? 这两句对仗,包含有句中对,“艰难”“苦恨”相对,“潦倒”“新停”相对,前者对之工整,后者则略显宽松。另外,“繁霜鬓”与“浊酒杯”又形成工对。但两句又不完全如此,七句“艰难苦恨”本是并列,因其“艰难苦恨”,故得“双鬓”星星,前后因果关系,“繁”则为形容词动用。八句“潦倒”“新停”非并列关系,而是因果关系,因为“潦倒”故得“新停”,新停者则是“浊酒杯”耳。如此,则七八句句式变作“四一二”与“二二三”,差异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如果不是先入为主,是很难察觉到这里是在用对仗的。这或也是老杜七言律诗尾联用对仗”精密“上的一种创造。 今日头条首发: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406173334495150642/?log_from=678e9e0c6cae1_1724385046436
|